当前位置:江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 文艺评论
文艺评论
时间与“人的发现”、民族国家建构——评《中国近现代小说中的时间问题研究》
发布时间:2021-11-15 16:4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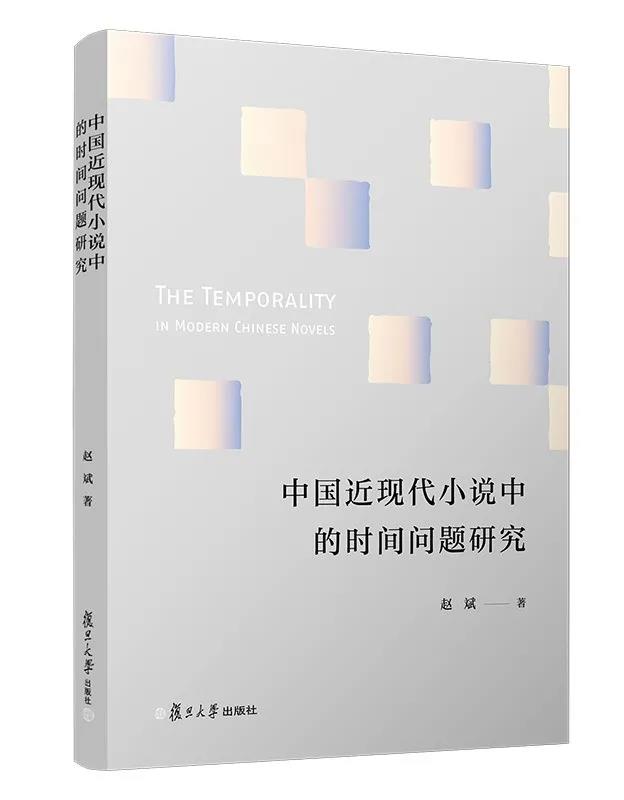
赵斌博士自2014年在中山大学攻读以来,主要从事时空叙事学、文人日记等专业研究,《中国近现代小说中的时间问题研究》是赵斌博士第一部专著,也是他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工作站完成的最新学术成果。
《中国近现代小说中的时间问题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版)出版以来,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山大学张均教授为该书所作序言《以时间为方法》在《文艺报》公开发表,然后被中国作家网等多家网络平台转载。《中国近现代小说中的时间问题研究》是一部关于小说转型研究的重要专著,极具个人化的研究理路让人耳目一新。并且,该书抓住了小说研究的关键问题——时间。
时间问题一直是小说创作的核心问题,其与现代性问题息息相关。时钟的发明,帮助人们建立这样一种时间信念:存在一个可度量其序列的世界,日常生活的节奏可以按照时钟的运转而演绎,时间成了调节身体机能的媒介。何时吃饭,不必等肚子饿,而是让钟表告诉我们;何时睡觉,不必等困了,而是由钟表加以确定。另一方面,指南针、星盘、方向舵的发明使人类不断开通新的海上通道,空间意识不断增强。可测的时间和空间意识,动摇了原初永恒和无限的概念,代之以进步、求新、求变等概念,人类进入了由“过去、现在、未来”并置的不断更替的线性历史时间。《中国近现代小说中的时间问题研究》将“时间问题”与“中国现代小说的发生”相关联,对中国小说现代转型这一问题进行本源性探索,从“缀段”的空间叙事,到个人的时间叙事,梳理了从晚清到“五四”小说流变的内在机理,并重新诠释了“人的发现”、民族国家认同等问题。
赵斌博士拈出浦安迪的“缀段性”概念,阐释了晚清小说的空间叙事,不仅阐明了“说书人”“史官”“名士”对“缀段”结构产生的作用,还从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性”思维方式出发,点明了“这种整体意识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感通’的宇宙观念一脉相承”。中国古典小说无时间性特征,唯“一治一乱的循环”,陷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善恶模式”。“缀段”结构即是这一“道德时间”的产物。
一直以来,“形如散沙”的“缀段”结构被看成是小说家思想落后的表征。赵斌博士却能从中国文化的思维模式剖析“缀段”让中国文人难以割舍的内因,展示了“传统”的强大影响力。诚如德国扬·阿斯曼所说:
假如巩固群体身份认同的知识没有储存于文字中的可能性,那么它只能存储于人的记忆中。这类知识要实现其在建构统一体、提供行动指南方面(即规范性的和定型性的)推动力,就必须首先具备这三个作用:存储、调取、传达,或是说是:诗的形式、仪式的展演和集体成员的共同参与。[1]
中国传统小说所显示的由不同成分组成,松散连在一起的片段缀合而成的情节特性,恰恰构成了诗的形式。叙述者自由进出,随意点评、旁逸斜出的叙事语调,源于说书人、史官、名士之风,这一文化记忆保证了晚清文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因此,在20世纪初期,伴随着中西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碰撞,新旧思想的冲突,循环时间受到西方线性时间的挑战,晚清、“五四”小说出现了再度空间化的回流。赵博士颇有建树地指出:再空间化改变了古典小说有头有尾的“满格时间”,成功转向了书写“横截面”式的现代小说结构模式。这一回流,也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小说在与传统难以割舍的血脉关联下的曲折前行。
赵斌博士将这一前行分为“外在情节时间叙事”和“内在主体时间叙事”,并认为,小说结构由外在的情节到内在的心理的“向内转”才是中国小说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赵斌博士在此区分了“新”“旧”时间,他认为,新、旧时间是一种现代性时间,包含着时间向未来无限延伸的认知。社会转型期的晚清,“五四”先觉者们对这种未来趋向的时间观充满无限的信任。伴随着列强的入侵,这种对自身现代化落后的焦虑演绎出向往未来、持续进步的时间意识。
最初的时间意识表现为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具体表现为晚清政治小说的“白日梦”叙事。这种“白日梦”叙事只是能够缓解新旧时间的断裂,“梦醒了却无路可走”。小说家们只是用“梦”迷醉自我,坚信不断进化的时间前方必然有光明的未来,然而,小说更多书写的是“梦”醒后的彷徨与沮丧。赵斌一针见血地看出了“维新”背后的“伪新”,“伪新”带有很大的欺骗性,最终导致了个人自由时间的腐化。“五四”时期,子君们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鲁迅《伤逝》),最后还是沦入了做饭、烧菜、与官太太们争斗的庸常时间中。赵斌博士不仅看到了憧憬背后的绝望,还看到了进步背后的假象。在他看来,时间容易让人产生幻象,认为“新”的一定比“旧”的好,这源于时间的有效性。拥有新思想的激进个体在庸常时间中,仍然陷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循环时间中,个人被还原了,社会却停滞不前。
由此,赵斌区分了“个人自由时间”和“个人公共时间”,援引了巴赫金的成长时间理论加以分析,提出:
个人成长时间无法逃离他所处的变迁的时代,历史时间投射到个人成长时间里,个人时间也在参与历史时间的建构。民族国家作为想象的命运共同体,需要个人公共时间参与,共同建构民族国家。[2]
个人的成长离不开社会、历史,个人成长时间与社会变迁的历史时间完美地融合。赵斌将个人成长与社会进步结合起来,指出脱离社会进步的个人维新是“伪新”,脱离个人成长的社会是孱弱的群体,只有个人的觉醒才能拯救民族国家;个人时间意识的觉醒,是人从蒙昧到文明的精神进化表征,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人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个人时间上,个人自由时间和个人公共时间构成了个人时间的两个维度,赵斌博士提出:
个人公共时间偏向于群体时间概念,个人自由时间偏向于个体时间概念。晚清的“新国民”偏向于群体概念。“五四”的“新人”偏向于个体概念,相应的,“国民”与“人”也是有区别的:“人”表达的是个体范畴,“民”属于“群”的范畴。“国民”是在拯救、建设新的“民族国家”的时代形势下产生的,因此,它剥夺了“人”的个性自由、取消“人”的独立性和自我意识。[3]
由此,赵斌以个人时间重新阐释了“人的发现”这一传统命题,个人公共时间进入历史的方式即革命,目的是建立一个新的民族“想象共同体”。在晚清、“五四”一些进步的革命性小说中,进步人物的革命生活时间是小说展现时代进步的具体表现,革命是作为推动时代进步的重要力量而出现的。进步的革命性小说按照线性进步时间组织故事时,必然把个人公共时间作为小说描写的重点。
赵斌得出结论:个人时间的取得预示着“人的发现”,在个人时间取得之前,人是传统的无时间的人。中国古典小说的个人是不能够自决的,其在物质上受束缚、奴役,在精神上受钳制、限制。拥有个人时间的现代人可以“自由地掌握自我时间”,换言之,拥有个人时间的现代人对个人时间的调配有了“自决”权,会重新调配人参与群体(历史)与个体(私下)的时间。由此,人的个人时间就分裂为个人公共时间和个人自由时间。个人公共时间是现代社会中的人参与社会发展进程的集体生活时间,包括个人参与政治革命的生活时间,参与社会文化改革的生活时间,参与社会经济建设的生活时间等。个人自由时间与个人公共时间是相对的,主要包括个人融入家庭、娱乐等私下的世俗生活时间。民族国家作为想象的命运共同体,就需要个人公共时间参与进来,共同建构民族国家。一句话,人要进入现代历史,建构现代历史。
小说的时间问题是一个需要不断挖掘的大问题,赵斌从时间角度重新审视了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他不仅从史的角度梳理了晚清、“五四”小说转型“缀段”叙事—外在情节时间叙事—内在主体时间叙事三个阶段,还将内在主体时间分为个人自由时间和个人公共时间,通过时间阐释了“人的发现”、民族国家建构等命题。这部专著既有对小说文本的细读,也有对社会历史思潮的宏观把握,将小说转型纳入了中国社会现代进程的历史脉络中,不但关注了个人在社会中的成长,而且将个人成长融入历史前行的轨道中。在赵斌看来,历史的宏大叙事是以牺牲个人成长为代价的。在历史宏大叙事下,个体的时间是庸常时间和日常时间,人是仍深受旧思想影响的“旧”人。只有当历史宏大叙事转为个人叙事,获得个人时间后,人才能自由地参与公共事务中,由此人才获得主体性,小说现代转型才得以发生。这一系列的论述,见出了赵斌作为青年学者的睿智和其作为知识分子的担当。赵斌在书写小说的历史的同时,也在展示小说的未来。作为新世纪的知识分子,我们也要秉承晚清、“五四”个人解放精神,将自身的发展融入为人民、为国家服务的宗旨中,为构建民族共同体,为实现“中国梦”奉献自己的青春与激情。
注释:
[1]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1页。
[2] 赵斌:《中国近现代小说中的时间问题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67页。
[3] 赵斌:《中国近现代小说中的时间问题研究》,第248页。
(作者单位:衡阳师范学院)





